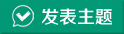谈到数字经济,数据隐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无独有偶,这也是6月26日一上午的核心议题,吸引了包括法国国务顾问、数据保护局前局长伊莎贝尔·法尔科·皮尔罗廷,苹果公司全球隐私资深总监简·霍华特、微软前首席经济学家普雷斯顿·迈克菲以及蚂蚁金服首席隐私官聂正军和首席知识产权法务官白建民等政商届的人一起探讨当下我们在隐私保护和数据治理方面面临的挑战。但不知道是议题本身的敏感性还是人物的敏感性,该议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闭门会议。
最后的环节是一个自由讨论的环节,有点儿像议事堂。那种积极踊跃的讨论甚至调动起了如我这般旁观者的亢奋情绪。你无法想象一个为期两天、高度消耗脑力的会议,到了最后这些动辄五六七十岁的经济学家们居然还老老实实坐在这儿听台上的演讲和对话,六位诺奖得主还剩下四位,听得比任何人都津津有味。这让人感动。
 茶歇期间经济学家们的讨论
茶歇期间经济学家们的讨论 在个小时的自由表达中,他们的核心关切主要是放在了数据隐私上。
忘了是哪位学者了,他提出了一个困惑:“如果说出现了违反了隐私条款的话,到底应该以多大的程度上去给企业施加罚金,罚金额应该多大?”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库斯·布伦纳梅尔:“我觉得这(数据隐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到底是不是要把一些数据隐私化,因为这些消费者很难去了解这些数据背后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当局来对公众说,这些是敏感数据,那些不是敏感数据。我不是说要FDA批准,但是当局应该有一些相应的机制、用不同的方法去评估,这一点我们要考量的。”
康奈尔大学副教授丛林:“我也是关注隐私这个问题,因为我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确实要区别开隐私和数据使用这两者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泄露的问题,有一些可能是不当心的泄露,还有就是对于数据的不公正的使用。我觉得我们缺失的一点,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些私有数据,我们怎么样去对人们进行赔偿,那些持有数据的人怎么向用户支付他们的这些数据。所以说我认为在实际操作上,我们确实会去做这样的区分,我们会去区分一个是私有化的数据,比如个人的个性,比如我的社会安全号码。还有一些可能是在平台上生成的信息,有多个参与者参与的信息。所以这些信息不是对我一个人隐私的,他可能是一个集体拥有的数据。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样去操作?这个可能是一种公共的这样的一个所拥有的数据,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普利斯顿大学教授熊伟:“Patrick(帕特里克·博尔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契约理论、公司金融、产业组织)刚才讲到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要用户能够同意,我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有些情况下,公众可能对这种同意也有一种厌恶感,当然你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决定是很难做的,有的时候你想说不,但是也不一定能够说‘不’,之前的嘉宾在演讲里也讲到这一点,没有人真的能够对微信说‘不’,因为你所有的朋友都在微信上,我们不需要同意微信的任何的要求,所以说对我来说,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去捆绑化。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捆绑性的话,他会把很多东西捆绑在一起,微信会给到你相应的信息,或者Facebook会相应的信息给到其他的服务提供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同意就是捆绑了很多你的私人信息的。如果我们能够去这个捆绑的话,我们的决策就做得更容易了,因为你只要给到Facebook决定使用你的信息,让它在Facebook上要用某些功能时去使用这个信息,而不是把这些信息卖给它或其他的公司。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同的决策。还有一位嘉宾在演讲当中也讲到了小程序问题,当你进到一个小程序的时候,你可能会做一个独立的决策,这个时候我们同意把这个数据给到它。在一个平台上,你经常要给到一些不同的独立的决策。你完全可以说‘不’,你有这个选择权说‘不’。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至少是目前为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哥伦比亚大学商业院教授王能:“关于隐私保护方面,我可能更加的乐观。我觉得在数据方面,在我们的数字经济当中,必须要更加的具有流动性,更加的具有生产力。而且,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大的一些困难,通过我们讨论的环节,在这两天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可能大家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希望除了我们这一次的讨论,在未来我们必须先迈出一步,至少我们是有所进展,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程度上要妥协。有文化上的差异,可能是价值观这方面的差异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是让我们的数据在欧洲、亚洲、美洲,如何很好的让这些数据流动起来,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更加实际的措施,比如说你在这个方面放弃一点,那个方面我妥协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相当于有第三方的独立的一方能够帮助我们统筹协调一下,这样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妥协,至少我们可以往前迈进一步。”
现场永远比文字生动,但现在也只能止步于此。
罗汉堂搭台,经济学家唱戏
 前面几排都是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们
前面几排都是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们 如果你在现场,你会发现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明显有别于其他会议,它给人一种感觉是“我搭台,你唱戏”。
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一再强调,罗汉堂不是阿里巴巴的罗汉堂,只是由阿里巴巴倡导成立的。这本身就表明了该会议的开放姿态,它思考的和想触及的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不仅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企业。它在去年成立时的使命宣言里说:“罗汉堂将秉承科学研究的开放精神,以正直、普惠、多元的原则独立运作。”
罗汉堂肩负的使命有两个:一个是理解数字技术如何帮助实现社会共同利益;另一个是帮助建立一个广泛的研究社区,聚合共识与力量,为解决新问题提供新范式。
从参加这个会议的本身感受来说,它的确在按照它所宣扬的那样做。我可能并不能从短短两天的会议本身总结出什么深刻的思想,因为很难全部消化。
仅就我个人的观察,罗汉堂无意在每一个议题上达成共识,它的作用是提供一个不同国家和文明的人济济一堂、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表达自己思想的平台——即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看待同一个问题时是如此的不同,无论是数字平台还是数据隐私,抑或是数字经济,因为文化差异、价值观差异和社会差异带来的思想的碰撞如惊涛骇浪——在互相了解、反驳的过程中又自然而然达成一些有限的共识。
正如罗汉堂宣言里所言:“此时,是把学术思想与实践洞见结合起来的时候了。”
“我觉得在未来需要有更多的交流,我们有很多一致的想法,但是我们也有不同的想法。”托马斯·萨金特老爷子在总结的时候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有不同的想法。虽然名字可能是一样的,比如说都叫汤姆,TA可能是一个人、一只猫、一个星球。对我们来说有不同的测量的方法,我们一定要挖得深一点,包括我们的机器学习,这些名称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挖掘下去(才是重要的)。”
马云主动避让同样值得肯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简直是在做慈善,对参会者而言。因为按照经验主义,有马云在的场合,他总是会吸引到媒体和摄像机的镜头,这就显著稀释了会议本身的意义,就像当年的乌镇饭局抢夺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本身议题的关注度一样。
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应该关注的宏大议题。
但马云也没闲着,在6月26日的傍晚,在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结束之时,他个人出资创办的马云公益基金会宣布给捐1亿元,成立“拉萨师专·马云教育基金会”,在西藏寻找和发现优秀的乡村教师、乡村校长和乡村师范生,帮是培养未来的乡村教师家,支持西藏教育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显然,马云的心早已飞到了离太阳更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