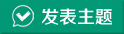文/成滋华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绕不过去的是中秋月饼。几十年都是这么过的,小时候,中秋月饼是家里做的糖饼,后来,都吃买的或单位发的现成的月饼。
现在吃月饼,也就吃那么一两块而已,一是因为普遍过甜,真是吃不了多少,二是觉得口感太腻。但一两块中秋月饼总是要吃的,感觉吃了月饼才算过了中秋这个节。
无论是几个人的小公司,还是几千人的大集团,中秋月饼,总是要发一发的。几天前,我从单位拎了两个铁盒子回来,是杏花楼的广式月饼,有豆沙、绿豆蓉、莲蓉、伍仁、奶椰、木瓜蓉几种。
小时候,中秋月饼是家里做的糖饼。面团包着白糖,再用擀面杖将其弄成巴掌大的圆饼,然后放在锅里烤。烤出来的糖饼滚烫;糖饼有些凉了才能吃,咬一口,一般都会咬到已经化成糖汁的白糖馅,这时候,糖汁往往也是很烫的。见不到这种糖饼也已经很多年了。
其实,月饼并非中秋节才有,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得卖,散装的、精装的,都有。但因为觉得月饼口感太甜、太腻,我从来没有主动买过当早餐、当零食什么的。
关于月饼的记忆,最美的是几十年前在苏北农村老家留下的。
面团里包白糖烤成的糖饼,对于以山芋稀饭、咸萝卜干为主食的人们来说,当然是一种难得的美味了。
那时的苏北盐城农村,村民们住的都还是茅草房。茅草房,墙是土坯砌成的,房顶是稻草做成的。村里唯一砖木结构的房子是地主家的,地主早已逃到台湾去了,那砖房变成了供销社的商店。
那时,村民们都是纯粹的农民。种田,养头猪、养几只鸡;没有人到什么地方打工,因为那时根本就无工可打。
上世纪70年代,苏北盐城农村村民们的生活还是原生态的。天空没有一丝雾霾,享受着干净的空气;池塘里的水是大家的生活用水,用木桶去池塘挑水回来放在大缸里;种的水稻、小麦、山芋、玉米之类的,一部分交公粮,剩下的留着自己吃;每家都有一块小自留田,种一些日常需要的蔬菜;家境好一点的人家,一般每一个星期可以吃一顿肉食。
每个星期,村里会有个集市。本村的人在集市上买或卖,邻村的人也会来到集市买或卖。大饼、油条也一定会在集市上出现,对于村里的孩子们来说,这两样便是顶级的美味。
村里有几条土路和外面的世界相连。有通往邻村的,最令人兴奋的是通往公社的,也就是通往现在的乡政府所在地的土路,那条路意味着可以去远方的城市。
1976年,我全家就经通往城市的土路去父亲工作的城市定居了。从此离开苏北盐城农村,村里的情形,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种种变化,就不得而知了。
(完)
2018年9月24日星期一